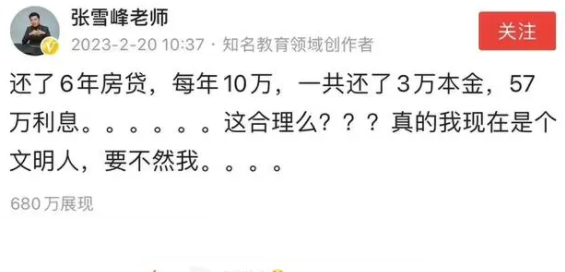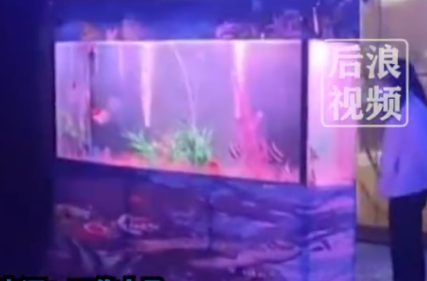《漫长的季节》被吐槽“爹味”浓 好内容还能留下多少呢?
导读:这样下去作品会变成怎么样? 正常逻辑,要改变现状应该去支持女性作者、女性向的作品,甚至致力于一个更包容的市场与大众审美。
02
为何无法共情?
今天要接受男性视角指控的,不仅限《漫长的季节》。
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。
男人负责公路旅行、探索宇宙,女人只有旁边干着急的份。
厌女。
《不止不休》。
女票苗苗戏份少工具化,又是厌女。
《满江红》。
电影里东窗事发,伪装成妓女的刺客瑶琴被带走。
沈腾对士兵高喊了一句——
“杀可以,别糟蹋她”。
很多人揪着这句台词:大男人、物化女性。
只看性别和台词,好像是那么回事。
问题是。
妓女,只是瑶琴“装”的职业,她更重要的真实身份,是刺杀秦桧的间谍。
回到正常的人性逻辑。
间谍被发现,最可能的心愿是什么?
参照《风声》被酷刑折磨到仅剩半条命的顾晓梦。
她最大的心愿,就是立刻被杀,既是结束痛苦,也是断绝更多泄密的可能。

于是。
顾晓梦看准机会,刻意咬军官的耳朵,让军官大喊,让外面的人误会。
于是。
当别人掏出枪的时候,军官才那么生气,因为审惯间谍的他,早就看穿了顾晓梦的心思。
看完这一段再来琢磨《满江红》沈腾的台词。
你还会觉得,那是一个男人在“道德绑架”一个女人?还是同为间谍的他们,为了刺杀而弃车保帅?
Sir觉得,不是创作者用了男性/女性视角,导致女性/男性观众难以代入。
恰恰相反。
当你过分关注所谓性别视角,去评判它是否足够平衡和公允时,才导致了更彻底的无法共情与代入。
简单化、二元论的思维固然是“爽”的,但也就隔绝了你与故事中的那些复杂的人物,幽微的人性产生真正的沟通与神交。
回到《漫长的季节》里举例。
2016年的沈墨,重回桦林报仇。
有人说,怎么大爷被杀的细节一点没拍?反而罪状更轻的大娘,却被沈墨恶狠狠地剪指甲、列举罪状?

哦,又是搞性别歧视那一套?
男的做了坏事,可以轻描淡写;女的只是帮凶,就要公开处刑。
进而又得出——
沈墨这个人,只是导演传达爹味和厌女的“工具人”。
这种潜在逻辑可能比审查更恐怖。
这是在要求一个不全能的角色,一个有创伤的受害者,为了给观众一个绝对正义的爽剧结局,就要完美、公平地对分配恨意与惩罚。
细想。
沈墨为什么恨大娘,她恨的只是大娘,还是大娘背后的广泛沉默?
大娘是不想帮,还是不能帮?
不能,仅仅是为了维系婚姻、被大爷精神控制?
想到这一层,Sir也困惑了。
于是又找了一些大爷的细节——
傅卫军给沈墨写的信,大爷为什么能看见?
傅卫军出狱前死在监狱,怎么也没人去查,骨灰直接就到大爷手里?
再结合大爷对马德胜说“我认识你领导”,对夜总会老板说“会带局长来”,对沈墨暗示:你早晚死我手里。
上一篇:杨紫申请强执拉夏贝尔网店25万元 我们应该呼吁企业加强自身的管理
下一篇:最后一页
-
 《漫长的季节》被吐槽“爹味”浓 好内容还能留下多少呢?2017-09-01 14:33:32这样下去作品会变成怎么样? 正常逻辑,要改变现状应该去支持女性作者、女性向的作品,甚至致力于一个更包容的市场与大众审美。
《漫长的季节》被吐槽“爹味”浓 好内容还能留下多少呢?2017-09-01 14:33:32这样下去作品会变成怎么样? 正常逻辑,要改变现状应该去支持女性作者、女性向的作品,甚至致力于一个更包容的市场与大众审美。 -
 杨紫申请强执拉夏贝尔网店25万元 我们应该呼吁企业加强自身的管理2017-09-01 14:33:32这项事件的发生,不仅直接损害了杨紫的权益,也暴露了一些企业对待代言人合同的不规范行为。代言人作为企业产品宣传的重要角色,合法权益的保障应该是企业的基本义务之一
杨紫申请强执拉夏贝尔网店25万元 我们应该呼吁企业加强自身的管理2017-09-01 14:33:32这项事件的发生,不仅直接损害了杨紫的权益,也暴露了一些企业对待代言人合同的不规范行为。代言人作为企业产品宣传的重要角色,合法权益的保障应该是企业的基本义务之一 -
 上海20岁女子被3万卖到安徽当新娘 网友纷纷谴责人贩子的行为2017-09-01 14:33:32王霜父子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,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。 奉贤法院检察官王彩表示: 这一事件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和讨论
上海20岁女子被3万卖到安徽当新娘 网友纷纷谴责人贩子的行为2017-09-01 14:33:32王霜父子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,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。 奉贤法院检察官王彩表示: 这一事件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-
 6岁娃意外死亡父亲收3万签谅解书 一起令人心痛的事情2017-09-01 14:33:32近日,河南南阳发生了一起令人心痛的事情。一名6岁的小男孩因为不幸被村里的墙柱砸死了。据孩子的妈妈李女士称,当时孩子正在和爷爷一起走路,孩子不小心抱住了墙柱,结果墙柱倒塌下来砸到了孩子的头,导致孩子当场死亡
6岁娃意外死亡父亲收3万签谅解书 一起令人心痛的事情2017-09-01 14:33:32近日,河南南阳发生了一起令人心痛的事情。一名6岁的小男孩因为不幸被村里的墙柱砸死了。据孩子的妈妈李女士称,当时孩子正在和爷爷一起走路,孩子不小心抱住了墙柱,结果墙柱倒塌下来砸到了孩子的头,导致孩子当场死亡